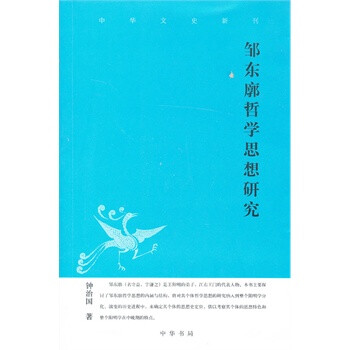
邹东廓哲学思想研究
李会富
摘 要:
邹东廓以戒惧工夫统摄格物、致知、静修、自然等其他工夫,以本体戒惧为致良知的基本方法,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发展为本体戒惧的学问。本体戒惧思想一方面强调“从心体上点检”,保任良知本体不受外染;另一方面又强调良知本体存在于发用流行之中,应在人伦日用上作工夫。它主张工夫无分于动静,戒惧即是自然,突出了阳明学即本体即工夫的学术传统。在阳明逝后门人思想各出歧路的学术背景下,这种用功方法成为传承阳明思想精神的一条正途和救治阳明后学学术流弊的一剂良药。
关键词:邹东廓;本体;戒惧;静修;自然
黄宗羲曾说:“姚江之学,惟江右得其传。”①而在江右王学众多学者中,真正能恪守师说而谨遵阳明宗旨者,莫过于邹东廓(1491—1562)。东廓,名守益,字谦之,是阳明在虔时收的得意弟子,也是阳明之后江右地区讲学活动的主要推动者。他既能谨守师说,为“同门之所不能及”②,又能匡正王门后学之流弊,推动阳明学的传播与发展,故而被学者尊为“王门宗子”③。在守护师说、匡正流弊、阐发王学的过程中,东廓结合自己对阳明思想的理解,体验出了一整套以本体戒惧为特色的为学用功方法。这一用功方法强调在本体上做戒慎恐惧的工夫,“以戒惧谨独为致良知之功”④。由此,本体戒惧思想便成为东廓之学的主导思想和一大特色。
一、戒慎恐惧便是致良知工夫
邹东廓的本体戒惧思想源自他对王阳明“致良知”工夫的理解。“致良知”是阳明为学的“正法眼藏”,也是阳明学的核心话题。王阳明曾将其称作“千古圣学之秘”,认为“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⑤,“致良知之外无学矣”⑥。东廓作为王学嫡传,也把致良知作为自己为学用功的宗旨,认为“圣门之教,以致良知为要”⑦。但是,在怎样致良知的问题上,东廓则有他自己的偏好。他认为,“不睹不闻是指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也”⑧;“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便是致良知工夫”⑨。时时致良知,也就是要时时戒慎恐惧。
为了说明戒慎恐惧在致良知工夫中的根本地位,邹东廓从阳明学的基本立场和运思逻辑出发,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在他看来,良知本体乃是天命之性,本是纯粹至善、昭昭灵灵的,自会发用流行,自是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但皆因世态的玷污、情欲的污染、意见的牵引,使得良知之发用流行有所倚着、有所遮蔽,于其本体尚有间隔,从而造成发而不和、行而不善,以至于沦为凡夫小人。因而,学者的为学工夫就是要保任本体,使诚性存存,使其在流行发用中贯通自如。那么,如何才能保任至善本体,使其自然流行呢?这就需要对良知本体时时警醒戒惧。他认为,古圣先贤之所以能成其為圣贤,就是因为他们“素位而行,不论出处,不分顺逆,只是戒惧勿离”⑩;而后人之所以迷失本性、遮蔽良知,也正是因为他们“不从戒慎恐惧处用力,而讨论辨析,想像忆度,以求深晓,故方其闲居,炯然不昧,及于对景,懵然莫择”(11)。因而,学者致其良知、学做圣人,必须纠正“戒惧工课有窒有断”(12)的错误,切实做戒慎恐惧的工夫。只要戒慎恐惧时时不离,在日用人伦庶物上时时不放松,就能全得良知本体,使日用人伦符合天则。
邹东廓在强调戒惧工夫的同时,并没有明确否定阳明学的其他用功方法。但在他看来,儒家经典所提出的诚意慎独、格物致知等其他所有用功方法都可归为戒慎恐惧,戒慎恐惧是其他用功方法的着力点和入手处。他说:“戒慎恐惧便是慎,不睹不闻、莫现莫显便是独。自戒惧之灵明无障便是致知,自戒惧之流贯而无亏便是格物。”(13)格物、致知、诚意、慎独等工夫名目,虽然表述不同,但实际上所指的内容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戒慎恐惧工夫。由此,他认为,“吾圣门正脉,以戒慎恐惧求致中和为准的。”(14)“即此便是自得,即此便是悟,别无一种机窍也”(15)。这便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归为戒惧之学,将戒慎恐惧作为致良知工夫的实际内容和根本方法。
二、点检心体的戒惧功法
既然戒慎恐惧是致良知之实功,那么学者应该如何戒慎恐惧呢?对此,邹东廓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做出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正确实践戒惧工夫的用功方法,即点检心体的戒惧功法。
(一)戒惧工夫的最高层次是本体戒惧。在东廓看来,自《中庸》提出“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以来,历代学者论述“戒慎恐惧”者可谓繁多,主张“戒惧之功”者也不在少数,然而,真正得戒惧工夫之要领者却寥寥无几。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戒惧工夫虽是可简明表述、易于理解、直接实践的易简工夫,但它却有高低层次之分,许多学者对戒惧工夫的践行只是低层次的。他说:“戒惧之功,命名虽同,而血脉各异。戒惧于事,识事而不识念;戒惧于念,识念而不识本体。本体戒惧,不睹不闻,常规常矩,常德常灵,则冲漠无朕,未应非先,万象森然,已应非后,念虑事为一以贯之,是为全生全归、仁孝之极。”(16)这就是说,尽管许多学者都在言说戒惧、践行戒惧,但实际上,他们所谓戒惧工夫却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戒惧于事为、戒惧于念虑与本体戒惧。这三个层次虽然都叫“戒惧”,但本质上属于三种不同的用功方法。从体用关系来看,良知本体是念虑、事为得以合乎天则的博溥源泉,是发育峻极的根本,而念虑则是本体之发用,事为则是念虑之实现。戒惧于事为与戒惧于念虑都不识良知本体,因而都是有所偏颇的用功方法,都属于较低层次的戒惧工夫。唯有本体戒惧,才可以使良知本体不受障蔽,使念虑事为发而中节,才是正确的戒惧之功,才是戒惧功夫的最高层次。
(二)本体戒惧须“从心体上点检”。东廓所谓本体戒惧,是一种保任本体的工夫,突出了良知本体在为学次序中的首要地位。而按照阳明学的观点,良知本体即是人的心体;直接在本体上作工夫,就是直接在心体上作工夫。因而东廓主张,本体戒惧工夫必须把人的心体作为为学工夫的下手处,直接“从心体上点检”。他曾结合自己的修行体验,通过与“事上点检”相比较对此作出说明。他说:“近来悟得日用工夫尚是就事上点检,故有众寡,有大小;大事则慎,小则忽;对众则庄,寡则怠;是境迁而情异者也。虽欲不息,焉得而不息?若从心体上点检,使精明呈露,勿以意必障之,如日月之照楼台殿阁、粪壤污渠,境状万变,顺应如一,稍有障蔽,即与扫除,虽欲倾刻息之而不可得,方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之学。”(17)所谓“事上点检”,就是戒惧于事为,从事上体认。这种为学工夫是通过对事为酬酢的约束牵引、强索安排,使其不离于善,不从于恶。然而,事为酬酢千差万别,随境变迁,随时变化,因而,“事上点检”自是应接不暇、防不胜防,必然会有大慎小忽、众庄寡怠之弊,使得为学工夫事倍功半、劳累不堪,使得良知本体有起有灭、时有遮蔽。相对于“事上点检”这种下乘工夫,“从心体上点检”才是直呈本体的上乘功法。这种功法要求直接在心体上警醒省惕,不放纵,不拘迫,时时不敢怠慢,一有所蔽,随觉随扫,使人心本体始终不被纷繁杂乱的世俗物欲所蔽。东廓认为,如果真的做到“从心体上点检”,那么,良知本体就会常精常明,犹如日月一出,万境毕照,所有障蔽随即扫除,日用人伦、事为万变便皆是良知一脉之展现。因此,“从心体上点检”也就是致良知,也就是改过迁善,也就是致中和。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工夫。
(三)点检心体的本体戒惧即是持敬。将戒慎恐惧工夫归作持敬,是理学家對戒惧工夫的一般理解。在朱熹那里,戒惧工夫便属于“涵养用敬”的范畴;到阳明学产生后,戒惧工夫仍然内在地包含恭敬之心。东廓则在继承这一思想传统的基础上,直接将点检心体的本体戒惧与持敬看作同一个工夫,认为“心有主宰,便是敬,便是礼;心无主宰,便是不敬,便是非礼”(18)。正是因为东廓对持敬功夫的重视,所以,黄宗羲称“先生之学,得力于敬”(19),钱明先生在划分阳明后学派系时也称东廓为“主敬派”(20)。然而,东廓以“主宰”讲敬,虽然在文字含义上与程颐、朱熹等人以“主一无适”解敬完全一致,但是在实际功法上却与他们有着根本不同:程朱理学的“主一无适”是指对未发心体的涵养守护,而东廓所谓“心有主宰”则是指良知本体的不被遮蔽、自作主宰。在东廓看来,唯有能明辨是非、自觉自行的良知本体,才是人心的灵明或主宰;相应地,“心有主宰”的持敬工夫,也只能是在点检心体的戒惧工夫下保持时时警惕、事事警醒,使良知本体常精常明、常戒常惧,无往而不流行。他说:“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戒慎恐惧,常精常明,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视民之有财,若吾家之蓄积也,乌得而不节?视民之有技,若吾家之秀也,乌得而不爱?视民之有力,若吾家之蚤作而暮息也,乌得而不时?”(21)又说:“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于私欲也。故出门使民,造次颠沛,参前倚横,无往非戒惧之流行,方是须臾不离。”(22)持敬就是要使良知不杂于私欲尘俗,也就是要点检心体、戒慎恐惧,须臾不离。在他看来,有了这种持敬工夫,人伦庶物、治国理政就都会发于良知、合乎天理、无不中节。所以他说:“圣门修己以安百姓之功,只是一敬字。”(23)又说:“圣门之教,只在修己以敬。”(24)这样,“修己以敬”的持敬工夫便与点检心体的戒惧工夫融合为一,它们同为古人参前倚衡、颠沛流离所不离不弃的“圣门要旨”或“圣门正脉”。
三、人伦日用的“见在工夫”
东廓对本体工夫的重视,并不是离开人伦日用而只在本体上用功,而是将本体工夫贯彻于人伦日用之中。换言之,他所谓本体戒惧,既是从本体上点检的工夫,也是人伦日用上的“见在工夫”。
(一)本体戒惧是一种日用“实功”,需要在人伦日用中实行实践。在东廓看来,良知固然有体用之分,寂然不动者为其体,感而遂通者为其用,但是,“动静无二时,体用无二界”(25),体与用既不是两种状态,也不是两个时段,更不是两个东西,而是同一良知的两个特性,二者是合一的。他说:“指其寂然处,谓之未发之中,谓之所存者神,谓之廓然而大公;指其感通处,谓之已发之和,谓之所过者化,谓之物来而顺应。体用非二物也。”(26)指其体,则用在其中;指其用,则体在其中。并不存在一个用外之体或用前之体,不存在一个已发之前的未发。良知本体无时不在发用流行,也只在其发用流行中呈现。良知流行发用在外便是人伦日用,所以本体戒惧工夫不能离开人伦日用、酬酢万变,而恰恰要在人伦日用、酬酢万变中戒慎恐惧。他说:“古之人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真诚恻怛,无须臾之离,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往非盎然仁体。大公为中,顺应为和,裁成为位,辅相为育,直是朴朴实实日用学问,不是虚谈。”(27)这就是说,古人戒惧工夫都在事亲事天的日常生活中时时运用,都是实实在在的“日用学问”。“学不离事,事不离学”(28),只要时时事事都从吾心灵明处戒慎恐惧,“日用三千三百”就会都从此流行。
东廓这种重视日常人伦的为学工夫是对阳明戒惧工夫的继承。阳明曾明确反对“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29)的做法,认为戒惧工夫必须贯彻在礼乐刑政等日常人伦事物中,离开了礼乐刑政等日常人伦事物,戒惧工夫就会变成悬空无基的摆设。东廓完全沿袭了阳明这一思想,也认为“圣门之学,未有不行而可以为学者”(30)。他把本体戒惧工夫看作一种在日用人伦中实修实行、贯彻到底的“实学”“实功”,反复强调“实学”工夫的重要性,要求学者在日常生活中切切实实勤下工夫、勤修不已。他认为,“学问之功,必从实地上做起。非悬空超脱可入实地,工夫只从孝弟真切处学。”(31)只有在日用酬酢中实行伦常、实用其力,才能将戒惧工夫落到实处,才是真正的本体戒惧工夫。所以他说:“穿衣吃饭,步步皆实学。”(32)在此基础上,东廓将学者为学用功所得的体验见识分为“虚见”和“实见”两种。凡“比拟文义,依凭言语,以博闻强记测度景象”(33)者,皆属“虚见”;唯有在日常人伦中实行践履、实有所得者,方为“实见”。“虚见者,如门外而谈堂,堂下而谈室,虽百猜百中,终非真实。实见者,在门谈门,在堂谈堂,在室谈室,横说直说,皆是真实不诳语矣。”(34)本体戒惧工夫,恰恰要从日常生活的“实地”上做起,“从四时常行、百物常生处见太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处见真性”(35),在人伦道德、礼义纲常的“实学”“实功”中修证本体、体得“实见”。
(二)本体戒惧是一种“见在工夫”,需要即时运用、当下修行。为了强调本体戒惧工夫的实在性和不可间断性,东廓又提出了“见在工夫”的说法。他说:“戒慎恐惧,顾諟明命,便是朴朴实实见在工夫。”(36)所谓“见在工夫”,就是将戒惧工夫用在当下,不往前强索,也不往后放纵。在当下的洒扫应对、行住坐卧中切实用工,使得本体随时戒惧,从不间断,这样才能保证戒惧工夫是当下实行的实功。在他看来,“心中纷扰,只是将迎之累。若能时时照顾见在工夫,如临深履薄,即闲思杂虑自不能容。”(37)心中的闲思杂念当下去除,使良知本体在每个“当下”都精明常照,戒惧工夫在每个“当下”都不放过,这样就可以使心中常自戒惧,使良知常贯日用。所以,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时时不肯放过,这工夫方精。”(38)无论是居处,还是执事或与人,每时每刻都戒慎恐惧,“不肯放过”,当下事为,当下戒惧,这样的工夫才是真正的“精一”工夫,才是圣学用功的正宗。
按照东廓的这种理解,真正的戒慎恐惧之功乃是一种简易直接的当下工夫,它需要在实际的当下修行中遵循和体验,不能单靠语言文字的辨析说理而讲明白。在他看来,单纯对本体或工夫的讨论辨析、想像臆度,不但无助于工夫的实行,而且会妨碍本体的流行,因而都不是真正的戒慎恐惧工夫。他曾向别人讲解戒惧工夫说:“诸君试验心体,是放纵的,是不放纵的。若是放纵的,添个戒惧,却是加了一物。若是不放纵的,则戒惧是复还本体。年来一种高妙,口谭不思不勉、从容中道精蕴,却怕戒惧拘束,如流落三家村里,争描画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于自家受用,无丝毫干涉。”(39)这里,戒惧工夫被表述为对心体的存复,也就是要时刻点检心体,使其不放纵流失。这是一个在内容上很简单而在实践上却需长期坚持的工夫,其关键不在于内容的表述,而在于当下实行、时时用功、须臾不离。因此,他对那些对为学工夫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却又害怕戒惧工夫拘束的人给予批评,称他们如同流落到三家村里,却描画“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虽然可以描画的富丽堂皇,却于自己毫无受用,终究与自己“无丝毫干涉”。
四、戒惧工夫统摄静修
静修工夫是宋明理学的一种常用工夫,陽明学更是对静修工夫格外偏爱。尽管阳明在不同时期对静修工夫有不同认识,但他一生从未放弃静修,其学术经历中的几次重大转折都与静修密切相关。阳明之后,聂双江、罗念庵等王门学者更是以静修工夫作为致良知的根本方法。东廓以本体戒惧为工夫要领,也对阳明学的静修工夫作了阐释,对部分王门学者的主静倾向给予回应。通过这些阐释和回应,他将阳明学的静修工夫统摄于其本体戒惧思想。
(一)在继承阳明晚年思想的基础上,明确主张工夫“无分于动静”,将静修工夫统摄于本体戒惧。阳明早期的为学工夫有明显的喜静厌动倾向,但是,随着其思想的成熟,静修在其工夫论中的地位逐渐弱化。到他提倡诚意工夫以后,静修变成了其为学工夫的手段之一,心体流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动静合一论成为其基本观点,静修工夫便与致良知合一了。东廓对静修工夫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阳明晚年的思想。在他看来,良知本体时时流行,“昼夜不息,与天同运,与川同流”(40),并不存在一个绝对静止不动的状态。本体即在流行之中,未发即在已发之中;良知本体常寂常感,无分于动静。所以,为学工夫应该时时扩充本体,“必有事焉,无分于动静”(41)。如果工夫有动静之分,就会使内外寂感支离分解,要么在事为上点检,涉于逐外,要么脱略事为,沦为玄虚光景。这种为学方法,“学则交换,时须有接续,虽妙手不能措巧”(42),难免会在用功过程中忽动忽静,手忙脚乱,不得要领。因而,偏内偏静与偏外偏动都见性未透,都不是圣学用功的正确方法。
尽管东廓反对“动静有二时、体用有二界”的主静工夫,但他并没有彻底否定自北宋周敦颐、程颢以来的静修传统,而是在肯定“濂溪、明道二先生,真得邹鲁不传之绪”(43)的同时,对他们的静修工夫作出了新的诠释。在他看来,濂溪所谓“主静”不是离动求静,而是“无欲故静”,是在摒除各种欲念杂虑的修养工夫中使心体时时呈露,时时流行,不为外物所动。就其时时流行而言,是静中有动;就其不为外物所动而言,是动中有静。所以他说:“元公谓‘静而无静,动而无动,其善发良心之神乎!”(44)明道所谓“定性”之学,主“动亦定,静亦定”,也是“内外合一、动静两忘之学”(45),并非“杜绝人事,闭门静坐”,也不是“先习静以至于动静两忘”(46)。而真正的主静寡欲工夫,应当是心体常自警醒,常做“必有事”的工夫,使良知本体能不染物欲、流行自如。这样,东廓便把静修工夫归为他一贯坚持的本体戒惧。他说:“学者果能戒慎恐惧,实用其力,不使自私用智之障得以害之,则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大公,常顺应,若明镜莹然,万象毕照,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矣。主静寡欲,皆致良知之别名也。说致良知,即不消言主静;言主静,即不消言戒慎恐惧。盖其名言虽异,血脉则同,不相假借,不相衬贴,而工夫具足。”(47)主静寡欲与戒慎恐惧、致良知是同一个工夫。离开了戒慎恐惧,也就无所谓主静寡欲。戒慎恐惧,本体常精常明,不动于物欲,不涉于意见,这便是真正的“静”。
(二)从本体戒惧思想出发,对以聂双江等人为代表的主静归寂派进行辨难批驳,阐发自己对静修工夫的正确理解。与东廓一样,双江也认为良知流行有体有用,有未发有已发,反对在事为上点检,主张在本体上用功。但与东廓的体在用中、体用合一论不同,双江主张心有定体,体在用先,所以为学工夫固然不应只在事为上点检,但也不应像东廓那样在后天的日用酬酢上求本体,而应该直接在先天本体上用功,在复归本体、良知澄明之后,则其发用流行自会无不中节,犹如镜之照物,镜体澄明,则往来事物妍媸毕现。这种直归本体的方法,就是主静归寂。东廓对双江的主静归寂工夫提出明确反对。他在《简复聂双江》中说:“吾兄悯学者格物之误陷于义袭,却提出良知头脑,使就集义上用功,可谓良工苦心矣。而遂谓格物无所用其功,则矫枉过直,其于‘致知在格物五字,终有未莹。”(48)这就是说,双江强调直接在本体上用功,这抓住了“良知头脑”,可以救治当时学者的脱离良知本体的“义袭”之病,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双江抛却日用、脱略事为,直归本体,以为“格物无工夫”,则是“矫枉过直”,“终有未莹”,违背师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中和寂感通一无二,在格物工夫中求其本体,在酬酢事为中使良知呈现。
在他写给双江的另一封信《再简双江》中,他又将评论靳两城(名学颜,字子愚,号两城,山东济宁人)的一些论述向双江复述,以示两城偏内偏静之弊,试图以此点化双江。两城“大意主于收视敛听、一尘不撄、不波不兴为未发之时。当此不撄不兴,意尚未动,吾儒谓之存存,存存则意发即诚。”(49)这种用功方法与双江主静归寂相似,都是探求日用酬酢之前的未发之体。东廓对此评论说:“收视是谁收?敛听是谁敛?即是戒惧工课。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脉。”(50)他认为,本体工夫通一无二,收视敛听本身就是良知之发用,应当时时戒慎恐惧,时时做“见在工夫”,当下致其良知,从“四时常行、百物常生”处体认本体。“果能戒慎恐惧,保此本体,不以世情一毫自污,不以气质一毫自杂,不以闻见推测一毫自凿,方是合德合明、皜皜肫肫宗旨。若倚于感则为逐外,倚于寂则为专内,虽高下殊科,其病于本性均也。”(51)在他看来,以双江等人为代表的主静工夫属于“倚于寂则为专内”,并不能求得良知本体。保任本体的正确做法应为“戒慎恐惧”;只有时时戒慎恐惧,不使良知本体受世情气质的污杂,才是真正的体认良知本体的工夫。由此,东廓的静修工夫便与聂双江等主静归寂派的静修工夫有根本不同。静修工夫在东廓这里,归根到底仍是戒慎恐惧。
五、本体戒惧即自然流行
良知自然流行的观点,是阳明学的重要观点。无论阳明本人,还是龙溪、心斋等王门弟子,都反复强调良知自然流行的重要意义。东廓坚守师门宗旨,也强调良知的自然流行,并用自然流行去阐述他的本体戒惧思想。他认为,本体戒惧即是良知自戒自惧、自然流行,它与良知学的“自然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一)良知本体原自戒惧。阳明本人认为,良知具有自然流行的本性;如果没有物欲的污染和人为的干预,良知本体会自然发用流行,作为其发用流行的人伦日用自然会发而中节,这不需要任何的人为安排或强制力索。阳明后学中许多学者也都强调良知流行的自然性;无论是浙中王学,还是泰州王学,乃至江右王学,其主流都赞成良知本体不涉安排、自然流行。其中,浙中龙溪一脉,强调直悟本体便是工夫,本体一悟,则良知自然流行;泰州心斋一脉则强调“百姓日用即道”,认为致良知就应该顺其自然流行;江右双江、念庵则以为只要主静归寂复得本体,则良知本体自然会发而中节,所以“格物无工夫”。东廓作为“王门宗子”,继承了这一师门宗旨,同时又对其作了自己的独特发挥。在他看来,“良知本体原自精明,故命之曰觉;原自真实,故命之曰诚;原自警惕,故命之曰敬,曰戒惧。”(52)它本就是“精明”“真实”、至诚不虚的,“本自廓然大公,本自物来顺应,本自无我,本自无欲,本自无拣择,本自无昏昧放逸”(53)。换言之,良知本体本就具有“警惕”“戒惧”的功用,包含知是知非、发而中节的特性;戒慎恐惧不仅不与良知本体的自然流行相冲突,而且本就是良知本体的自然状态。这就从本体论上保证了戒惧工夫的先天自然性,化解了本体戒惧与自然流行之间的内在张力。
(二)本体戒惧才能自然流行。东廓不仅在本然意义上将本体戒惧看作良知本有的自然属性,而且在实然意义上将本体戒惧看作良知自然流行的充要条件。在东廓看来,普通人的良知之所以不能自然流行,就是因为戒惧工夫有间断,从而使良知本体受到世情的牵离、物欲的障蔽;而要克服这一弊病,就必须勤作本体戒惧之功,常“从心体上点检”,造次颠沛不离。他说:“若戒慎恐惧不懈其功,则常精常明,无许多病痛。特恐工夫少懈,则为我、为欲、为昏、为放,虽欲不拣择,有不可得尔。”(54)在日常的实际修行中,只要本体戒惧工夫毫不间断,良知就会自然流行;也只有本体戒惧工夫毫不间断,良知才会自然流行。本体戒惧是保持或恢复良知本然状态、保证良知本体自然流行的根本工夫。为此,东廓曾专门批评时人盲目追求“自然”而忽视本体戒惧工夫的做法。他说:“近来讲学,多是意兴,于戒惧实功,多不着力,便以为妨碍自然本体。故精神浮泛,全无归根立命处。”(55)“迩来学者以因循为平等,以严密为过当,于古人戒惧瑟僴几若长物,恐非自然宗旨。”(56)那种将戒惧与自然相对立、不做戒惧实功而一味追求“自然”的做法,只是“意兴”,是意念的放纵。它只会使精神浮泛不实,使学问虚悬无根,使行为任情恣肆。这既违背了良知本体的自然本性,也不是保任良知本体的正确方法,因而并不是真正的“自然宗旨”。
(三)本體戒惧乃自戒自惧。尽管东廓批评脱离戒惧的“自然”工夫,强调时时刻刻在本体上戒惧、“从心体上点检”;但在他看来,这种点检心体的戒惧工夫并不能使良知本体有所增损,也不是用一心去制服另一心,更不是用一个外在的力量去作用于良知本体,它归根到底仍要在良知本体的自然流行中运用,仍是良知本体的自戒自惧、自然流行。它拒绝一切人为安排,排斥在事为、念虑上求索。因此,东廓在反对脱离戒惧实功而盲目追求“自然”的同时,也反对“点检于事为,照管于念虑”(57)的不“自然”的做法,反对脱离自然的戒惧工夫。东廓的这一思想在他对季彭山“龙惕说”的辩驳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彭山乃浙中王门的重要学者,曾作《龙惕书》以救治当时以自然为宗者流于物欲之弊。他认为,自然是“顺理之名”、“流行之势”,“惕若者,自然之主宰”(58)。只有惕若谨独,才能心有主宰;内有主宰,外才能自然顺应。所以,“圣人之学,不贵自然,而贵于谨独。正恐一入自然,则易流于欲耳。”(59)彭山的工夫与东廓非常相似,他们都强调戒惧谨独,都主张在本体上常自警惕;但与东廓强调内外合一不同,彭山偏重内在警惕工夫,强调内心主宰作用。在东廓看来,彭山“忧近时学者失自然宗旨,流于物欲,特揭龙德之警惕变化以箴砭之,可谓良工苦心矣”(60),但他过分偏重内在主宰,而忽视了良知本体的自然流行,故于“警惕变化”与“自然变化”的认识仍有偏颇。东廓认为,“警惕变化、自然变化,其旨初无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滞;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荡。”(61)因而,警惕与自然不能分开,戒惧工夫与自然流行是一体的,其宗旨完全一致。换言之,本体戒惧工夫,既是“从心体上点检”、在本体上戒惧,又是心体的自我点检、本体的自戒自惧。本体是工夫的源泉和依据,工夫是本体的流行和发现,“做不得工夫不是本体,合不得本体不是工夫”(62)。所以东廓说:“自戒自惧,顾諟明命,正是圣门相传兢兢脉络。”(63)只有这种“自戒自惧”的本体戒惧,才是致良知的正确功法,才是真正的“自然宗旨”,才是数千年来圣门相传的工夫真谛。
戒惧问题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戒惧功法是宋明理学心性修养的重要法门。从整个理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戒惧功夫日益突出的过程。在程朱理学那里,《中庸》所说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还仅被看作一种内在涵养的未发工夫;而王阳明则将其析为戒慎恐惧与不睹不闻两个方面,格外突出了其未发与已发相融贯、本体与工夫相统一的鲜明特性。邹东廓的本体戒惧思想,既忠实继承了王阳明的致良知宗旨,又沿着阳明的理路做了深入发挥。它一方面强调要在良知本体上用功,应切实保任良知本体不受外染,另一方面又强调良知本体就在发用流行之中,应在日用人伦中做工夫;一方面强调要时时戒慎恐惧,使良知本体常精常明,另一方面又强调良知本自精明、本自戒惧,戒惧工夫即良知之自然发用。在阳明逝后门人思想各出歧路的学术背景下,这种既重视良知本体、又重视当下实功的用功方法,成为传承阳明思想精神的一条正途和救治阳明后学学术偏弊的一剂良药。同时,东廓对戒惧工夫的详细辨释,也大大丰富了理学戒惧思想的学术内涵,进而将宋明理学的戒惧工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 注 释 】
①④(19)(35)(39)(58)(59)沈善洪:《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16、381、392、392—393、310、310页。
②王畿:《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页。
③以东廓为王门正宗嫡传,是中晚明诸多学者的一致看法。早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是时东廓仍健在),吕怀便称他为“阳明先生嫡派”(吕怀:《东廓邹先生文集序》,载《邹守益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0页)。江右王学的另一重要代表陈明水也说当时“同门之士咸以曾子推之”,并认为“东廓用工笃实精密,其语良知本体,真与皜皜同见,海内同志赖焉”(陈九川:《大司成东廓邹公七十序》,《明水陈先生文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可见,东廓在世之时,就已被同门学者推为阳明嫡传。后来,其弟子马森也说:“东廓先生受学师门,独得其宗。”(马森:《东廓邹先生文集序》,载《邹守益集》,第1338页)明末黄宗羲则缵承前说而申明之曰:“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一》)直至现代,冈田武彦、陈来等学者仍以东廓为王门“正统派”的代表(参见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3—104页。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334页)。牟宗三、蔡仁厚等人也明确指出江右王门中“尤以邹东廓为最纯正”(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为“江右王门之正嫡”(蔡仁厚:《江右王门何黄二先生学行述略》,吴光主编:《阳明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⑤⑥(29)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90、280、37页。
⑦⑧⑨⑩(11)(12)(14)(15)(17)(18)(21)(22)(23)(24)(25)(26)(27)(28)(30)(32)(33)(34)(43)(45)(46)(47)(48)(49)(50)(51)(52)(53)(54)(55)(57)(60)(61)邹守益:《邹守益集》,第514、522、677、664、556、573、551、573、619、506、507、515、504、515、542、497、558、660、500、504、504、504、506、506、506、497、540、541、541、542、650、512、512、551、551、518、519页。
(13)(16)(31)(36)(37)(38)(40)(41)(42)(44)(56)(62)(63)邹守益:《东廓先生要语》,《邹氏学脉》卷一,载《续修四库全书》第9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7、481、489、485、483、486、491、491、491、491、484、483、487页。
(20)参见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151页。
此文由 科学育儿网-资讯编辑,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科学育儿网 > 资讯 » 邹东廓本体戒惧思想探析









